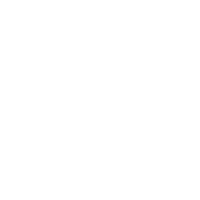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论文(第2页)
本文共计7463个字,预计阅读时长25分钟。【 字体:大 中 小 】
二、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现代语言哲学颠覆了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是我们在世的居所,并且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语言聚合现象的翻译研究首先要建立在语言学之上,但翻译不仅仅是一项语言行为,它更涉及到语言本身就已经包含的文化问题,翻译的文化视域在本质上赋予翻译行为一种合法性,因为将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翻译文本参照物不应该是源文本,而是翻译文本所处的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以及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翻译是一个以译语来消化、吸收“异”的过程,翻译转移、吸收原作的“异”以促进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同时,被翻译和转移的“异”在译语文化中获得新生,因此,文学翻译具有再创造性和意义再生性,需要突显译者的主体性。同时梅肖尼克和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均强调文学翻译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有必要在文学翻译诗学建构中把文学翻译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考量。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翻译绝不能随意而为,它的要求极为明确,即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得歪曲。因此语言哲学背景下建构文学翻译诗学必须考虑语言、文化和翻译伦理三个维度,缺一不可。1.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从本质上说,主体性是人活动的能动性问题。“人之存在的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1]翻译诗学是有关文学翻译的诗学,而文学翻译的过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二度创作”过程,梅肖尼克翻译诗学提出的“中心偏移”说强调译作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延长源语作品的价值,为此,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2],是一个译者选择和再创造的过程。这样才能使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纳进新鲜空气,从而使源语作品的艺术生命在新的氛围里得到重新锻造。为此,文学翻译诗学需要确立译者的主体存在,译者作为主体的存在是文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翻译诗学的发展和译者主体性的显性冲动,中外译论中关于以“规定性”和“忠实性”为目标的理论就具有了一定的狭隘性,因为它们抹杀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全部的文学特殊性”。文学富含诗性,文学性的意蕴既隐身于语言,又超乎语言之外,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一方面包括对源语作者主体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包括译者能够以创造性的翻译再现源语文本的节奏,实现中心偏移。“在处理语篇的过程中,我们输入了我们自己的信念、知识、态度等。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的翻译都将反映出译者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观,即使自己尽量地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毫无疑问,在大多的科技文献、法律文献和行政文献的翻译工作中,这种风险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文化取向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潜入……只要涉及具有主观性的话语,对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诸种微妙的侧重肯定是千差万别的。”[3]由此可见,译者的主观体验和主体参与对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表达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翻译诗学的、文化的生成转换中,译者必须跳出传统译论中“忠实”的束缚。语言工具论排除了一切文学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有别于实用语的“诗语”。语言哲学维度下,语言本身具有“创造性”,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特别反对西方语言观中把语言当作人类可以任意取舍的制品和任意分解的工具,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和精神劳动(Energeia)”[4]。此外,语言还具有“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特性,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音调、色彩、生动性和氛围。每一段文字除却其字面及具体的含义外,如同每一段音乐一般,还有其不甚言表的蕴意,这也正是诗人意欲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之唯一所在,而这也正是这层蕴义,才是译者当致力反映的……为了道出文学作品的这种文学蕴义,首先要抓住它,光抓住它也还不够,还要重建它。”[5]翻译不是单纯的认知行为,而是施为性很强的目的行为,是创造意义上的“作”,即对源语意义的读取和对目的语意义的建构: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往往会在翻译策略中倾注自己对译语文化的想象,以增译、缩译、节译、改变甚至伪译等诗学变体手段,达到对阅读的抵制和积极干预;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通常会以译语文化为转移,译本成为了文化“他者”和审美文化的喻体。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解构了以“忠实”为归依的“同一性”,形成了双重或多重的“异质性”。它理解、阐释、传递意义,同时也创生和赋予意义,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2.明确文学翻译是一种意义再生过程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其任务是帮助人们了解另一种语言所设置的意义域。文学文本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系统,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和一成不变的。汪正龙认为:“在文学理解中读者面对文本也泯除了时间的沟壑,处于常读常新的‘共在’之中,在意义的反省中自我的构成与意义的构成是同时的。时间沟壑的消除和理解的当下性走向使历史理解与美学理解相近。”[1]翻译不断地建构语言世界,生成文本,是使原作的意义显现出来的过程,是一种创生意义的文化行为。译者阐释文学文本就是阐释文本所设计的可能世界,各以其情而有所得,各以其智而有所悟,所谓“诗无达诂”、“以意逆志”正说明了文本意义的非终极性和意义再生的必然性。随着时代的更迭,人们对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新的理解。利科曾经把源语文本比作一条不断延伸的“地平线”:作者的本意被他写下的文本所“占有”“、盗用”、“远化”或“异化”,历史的文本遗传下来,更加有一种远化的距离感和意义的遗失,今天的读者必然跟它有“文化的冲突”。阅读力图克服这种冲突,“复活”尘封在文字中的意义,也就是重新“占有”文本,但这必定是文本与读者共同形成的“地平线”,眼下的现实场景与历史的距离感相互交汇“,复活”难全“,遗失”难免[2]。加上译者在理解源语文本时存在多重性、兼容性和动态性,所谓“译雪莱使自己成为雪莱”,其实也是“使雪莱成为了自己”。由此看来,文学翻译必定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米歇尔·巴莱特(MicheleBarett)曾经说过:“如果把语言看做意义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拥有了自己的巨大生命力。”[3]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体现了梅肖尼克眼中翻译诗学的“历史性”,对于原作而言,翻译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的关系:“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翻译关系所具有的历史性在目的语当中生产出语义的、句法的物质,这种物质开始时局限在翻译的范围内,接着它会成为语言某些特性发展的因素……在这里所牵涉到的关系问题上,翻译的时刻与语言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同等重要。翻译作为一种全新关系,它只能扮演现代化的、全新的角色,但是某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却将某一文本的翻译视作形式和过时。”[4]文学翻译的语言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具有弹性、伸缩性、模糊性和多义性,给译者以很大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空间,“文学语言不是直白和一览无余的,留有较大的联想余地与空间,在书写‘空白’与语言尽情延伸中可能会歧义丛生,文学语言的微妙在含蓄的优雅中得以充分的体现。”[5]因此,在对文学语言的艺术品位和多义感受中,意义被延生着、创生着和改写着,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我们有所理解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6]


数学毕业论文答辩问题汇总
关于毕业论文若干问题的规定
物体论原理
生态哲学论文
具身认知理论下武术教学的哲学探究的论文
关于对现代逻辑中量词的逻辑哲学进行分析论文
浅析生态哲学理论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指导论文
《孟子》中的咸丘蒙之问的哲学思考
西方哲学史的论文
钢琴教学中的现代教育论文
面对现代西方哲学困惑的若干思考
意大利留学奖学金可以给怎样人士介绍
关于医学论文发表必须了解的12个词
SCI论文发表全流程解析概要
医学论文发表经验总结
毕业论文(设计)格式及打印装订要求
SCI论文发表的一些技巧分享
本科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
高级工程师该怎么发表论文
学术论文的写作要求及学术论文的写作注意事项